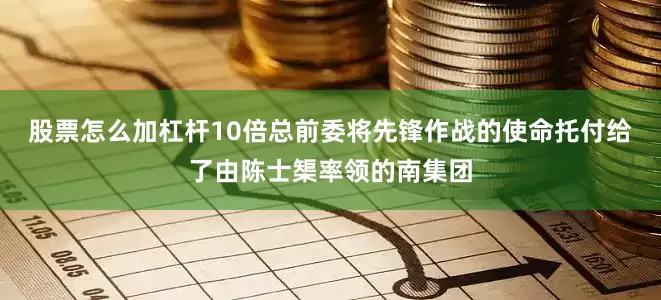
双堆集,不过是皖北平原上的一座平凡村落,其中居住着大约百户人家。1948年渐近年底之际,国共两军总计四十余万兵力,在此展开了长达23日的激战。那场战斗,打得天地为之变色,惨烈程度令人心惊肉跳。
最终,我军中原与华东野战部队携手协作,将兵力予以整合,尽管牺牲了超过三万名英勇战士,我们依然以顽强的意志,彻底击败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之众,其中四万敌军被直接歼灭。
凤凰卫视在制作《淮海战役全记录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,可谓是喜从天降,成功联络到了众多参与过此次战役的前辈老兵,更有部分老兵的子孙后代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。

昔时,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司令员秦基伟,不禁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。
战事落幕之后,地方政府动员民众清理战场,并颁布了奖励政策:每掩埋一名战士,赏赐5斤高粱;每掩埋一匹战马,则可得24斤高粱。第九纵队所攻克的张围子村虽规模不大,然而周边的村民们因协助掩埋工作,从政府手中领取了超过万斤的高粱作为回报。
那是在1948年的寒冬,中原与华东的野战军联合,于双堆集之地,与国民党最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了激战,彼时正是黄维指挥的第12兵团。
昔日的18军,堪称国军中五大猛将之一,亦为黄维12兵团的支柱力量。自土地革命时期至今,他们与我国军队交手无数,几乎每战皆能取得胜利或战成平局,未曾遭遇败绩。
因此,当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遭到中原野战军七个部队的严密包围之际,兵团指挥官黄维起初并未显得过分慌乱。
他心怀自信地揣测,此支部队卓越的作战实力,必能坚守至李延年部从北方驰援。届时,两部军队若能汇合,无论是突破困境或是反击敌人,均将势不可挡。

黄维坦言,我方的十二万精锐之师已严阵以待,静候中野的进攻。若非华野的粟裕将军派出五个纵队予以支援,中野恐怕还需再战两个月,方能攻克敌军。
12兵团配备的乃是美国式的摩托车化武器,此装备令黄维当时深感自豪与自信。
彼时,中原野战军历经千里跋涉,勇闯大别山,一番辗转激战,待得山势渐远,其人数已锐减至不足六万。手中最为精良的武器,不过是几门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山炮。在双堆集战役的头几天,中野的攻势虽勇猛,却未见显著战果,反而自身损失惨重,伤亡人数颇多。
我方华野部队需至少抽调两个纵队作为预备力量,以备不时之需。刘陈邓等人一旦有调用需求,即可即刻调动,确保随叫随到。
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,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粟裕迅速部署,令7纵、13纵以及特种兵纵队即刻启程。此次行动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领衔指挥,全体人员昼夜兼程,赶赴双堆集一线提供支援。

陈士榘率领三支纵队急速抵达双堆集,旋即与总前委进行商讨,表达了自己希望中野能够腾出一个指挥职位,以便自己能够领队,率领华野的战士们冲锋在前。
那时,中原野战军已将黄维兵团团团围困于三面要地。
在东集团中,汇聚了陈赓指挥的第四纵队、秦基伟所率领的第九纵队,以及来自豫皖苏地区的独立旅。整个庞大的事务集群,均由陈赓负责统筹指挥。
南集团下辖王近山率领的第六纵队以及陕南军区的第十二旅,两支部队均由王近山亲自统率。
西集团汇聚了杨勇领衔的第一纵队与陈锡联执掌的第三纵队,整体指挥工作由陈锡联全面负责。
诚然,陈士榘已不再执掌指挥之职。
随后,总前委作出了一项决策,将前来支援的华野三个纵队分别部署至三个不同的地域,而中野的陈赓、王近山、陈锡联则被委以重任,担任领队。至于陈士榘,他则被安排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,协助参谋长李达共同履行职责。

华野的参谋长陈士榘,其性情之火爆,素来遐迩闻名。听闻此等部署,他当场勃然变色,愤然表示,既然我们已无关紧要,那就即刻启程,向南进发,拦截敌军,正面交锋李延年。
在我父亲担任中野首席副手的同时,他还负责华野的事务,身兼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之职。目睹陈士榘情绪激动,他猛地一击桌面,直言不讳地要求陈士榘率领部队支援,主动承担主攻和攻坚任务,这实乃正道。然而,他严厉指出,陈士榘身为参谋长,身居高位,怎能因个人情绪而违背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?
不久后,经中野方面商议,决定让驻守双堆集南面的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退让一步,不再承担主攻任务。王近山不仅主动放弃了主攻阵地,还将6纵和陕南军区第12旅的指挥权一并交给了陈士榘,由陈士榘统一调度南线所有部队。
陈士榘遵照总前委的部署,将陈锐霆指挥的特纵一部划归陈赓所率东集团指挥。同时,他将周志坚的13纵调拨至陈锡联负责的西集团。陈士榘本人则率领成钧的7纵,与中野的6纵及陕南军区的第12旅并肩作战,共同构成了南集团。
当代人似乎难以理解我父亲那一代人的内心世界。他们这一辈人,历经战争的洗礼,在他们之间,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,或是争执几句,这都是人之常情。
归根结底,这些争论均旨在确保我军能够赢得战场上的胜利。当战火真正点燃,全国便如同一个大棋局,每个人均须跟随指挥者的步伐行动。无论指令指向何方,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,恪守军令,遵从指挥,在这方面绝无半点含糊。

经过重新部署,总前委将先锋作战的使命托付给了由陈士榘率领的南集团。此举与先前作战计划相异,彼时,主攻任务本应由陈赓负责的东集团承担。
在双堆集的激战中,粟裕肩负华野代理司令员的重任,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,他迅速调动了5个纵队增援,助力中野早日结束这场战役。
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,流传为千古佳话。在双堆集战役结束后,陈士榘同志目睹中野部队装备短缺,便即刻指示华野战士,将战场上所缴获的所有武器悉数赠予中野,甚至一枚子弹也未私自取走。
1948年12月5日,解放军发起了对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的全面进攻。在两大野战军的协同努力下,黄维兵团的防御阵地日渐缩小。仅仅四日后,其南翼防线已被压缩至仅剩大王庄的弹丸之地,与双堆集核心阵地相距不足一里。
若我军能一举攻克大王庄,此后无论是整治尖谷堆,抑或是征伐双堆集,都将变得更为得心应手。
在大王庄那片区域,两军士兵的激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,你来我往,阵地争夺激烈,场面之惨烈令人触目惊心。

率先挺进大王庄的是华野第七纵队的五十九团,然而,他们尚未来得及构筑防御工事,立足未稳,便遭到十八军连番猛烈的反击,被迫后撤。面对惨重的伤亡,华野7纵的成钧司令员迅速向中野6纵的王近山司令员发出求援信号。
此刻,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已陷入兵员枯竭的境地,所余唯有预备队中的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。这支部队,已成为王近山手中可供调遣至战场的最后力量。
原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营的教导员左三星,与记者畅谈往昔岁月。
在那个极其困苦的时刻,华野7纵向中野6纵提出了迫切的请求,渴望能尽快投入战场,充当战略预备力量。试想,若非形势万分紧急,成钧断然不会向王近山提出如此要求。
对于军人而言,荣誉便是他们的生命所在。我们这两支野战军在战场上并肩作战,竞争之激烈,自上至下,从指挥官到普通士兵,都如同置身于竞赛之中,无人愿意失手。成钧敢于提出这样的请求,无疑是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紧迫。
大王庄的敌军,与我所遭遇的过往之敌截然不同。我们一旦冲入敌阵,他们便如同割之不尽的韭菜般,一波接一波地奋勇扑来,誓死不退,接连不断地发起新的反攻。

中野六纵队的十六旅四十六团,作为一支新投入战场的队伍,在团长唐明春的率领下,沿着先前由其他部队挖掘的战壕,不断对大王庄发起了一场场猛烈的攻势。
战端开启之际,唐明春目睹了对面那群敌寇,他们一个个如同不要命一般,与唐明春同仇敌忾,豁出性命,凶悍无比。
驻守大王庄的部队隶属于黄维兵团第18军118师的33团,该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声名显赫,以战斗勇猛著称,因而被亲切地称为“老虎团”。
黄维部署33团驻防于大王庄,其用意昭然若揭,旨在使该精锐部队成为双堆集防线的稳固基石,坚守最后一道防线。

廖明哲少校,曾担任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营长一职。在与记者的交谈中,他分享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。
解放军屡次发起冲击,我们则屡次将他们击退。他们继续冲锋,我们再接再厉,将其逐退。在白日里,大王庄由我们掌控,然而夜幕降临,控制权便转至他们之手。
持续激战,大王庄阵地屡次易手,时而失守,时而收复,往返交锋,我依稀记得总计争夺了五轮。那场战斗的惨烈程度,简直令人触目惊心!
在经历了一日的激烈攻势后,中野6纵部队已成功控制了大王庄南部的众多村落。正当他们紧急修缮防御设施之际,敌方的炮兵部队却突然发炮,对他们展开了猛烈的火力反击。
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营的教导员左三星,曾这样追忆往昔:彼时,他正是该营的教导员。提及那段岁月,他的心中不禁涌动着无尽的感慨。
榴弹炮声声砰然炸响,我身受一枚炮弹猛烈冲击的余波,瞬间失去知觉,一片茫然,晕厥在地。大约过了数分钟光景,我迷蒙中听到通信员的呼喊声,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教导员的名字。我艰难地睁开双眼,只见阵地上的同袍已是寥寥无几。
恰在此时,敌军的炮火再次隆隆作响,倾泻而下。我自身毫发无损,然而,那位唤醒我的通信员却就此消失。在这短短的四天里,这已是第九位与我并肩作战的通信员,他们无一例外地未能幸免于难。
经过一番精心调整,中野六纵的十六旅四十六团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,决定兵分三路,分别向左、中、右三个方向,再次向敌人三十三团的最后一道防线发起猛攻。
正当部队准备采取行动之际,地面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定睛一看,原来竟有15辆敌军坦克,它们巧妙地绕过一道弯,悄无声息地逼近中野6纵16旅46团的侧翼和后方,随即从两侧展开了对46团的猛烈攻势。
副营长46团1营目睹战士们在坦克机枪的猛烈扫射下纷纷倒地,内心焦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,转头对教导员左三星急切地询问:“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?”
左三星简洁回应:“干掉,灭掉。”
中野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的勇士们,凭借着坚韧的体魄,手持手榴弹与炸药包,毅然将敌军发动的最后15辆反扑坦克悉数摧毁。
廖明哲,昔日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的少校营长,如此追忆道:
此刻,双方军队均已倾尽全力,胜负之局便在于谁能再坚持片刻,胜利的天平或许便会向其倾斜。
我团第三十三团的步兵全体投入了战斗,无一人缺席。随后,汽车兵、通讯兵、后勤保障兵、工程兵也纷纷拿起武器,加入了战斗的行列,甚至负责烹饪和饲养马匹的士兵也握枪奋战。
步兵的行列已空,连输送兵的战友们也毅然接替了战位。他们平日里主要从事的是搬运和抬运的工作,负责运送粮食、弹药等必需物资。
这支输送连汇聚了百余人,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四川的同乡。他们起初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征召为挑夫,随着抗战的胜利,部队进行重组,他们也就此转变为军人。然而,实事求是地说,这些人在平日里几乎从未接触过枪械。
手持枪械,口中与上级低声抱怨:“唉,我这命本该挑担,怎料竟遭遇此役?”边走边与长官并肩前行。唉,这场战争,真叫人难以言表……
这次可谓是敌33团的垂死一搏,然而结果显而易见,效果微乎其微。然而,黄维兵团第18军的顽强斗志,确实令中野和华野的战士们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敬佩之情。
中野第六纵队的司令员王近山,起初拥有一支由百余人组成的警卫连。然而,在激战中,这支队伍的成员锐减,最终仅剩十七人坚守阵地。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主编傅继俊为精心打磨《淮海战役史》一书,屡次深入昔日战场的各个角落。
春日时节,我踏入此地,目光所及便见那麦田。坦白讲,这片麦田的麦苗与别处迥异,它们生长得异常繁茂,既高且壮。
身旁站着一位同伴,我向他询问地面状况。他指向四周,说道:“你看,这里是一道横壕,那里是一道竖沟,纵横交错,弯弯曲曲,这些都是昔日军事行动中挖掘的战壕。”
战事结束后,尤其是那些来自国民党的战士,周围的村民便将他们的遗体移至战壕之中,随后撒上石灰,草草将其安葬。
我军攻克大王庄后,驻守于小王庄的黄维兵团第85军主力团即刻举起了白旗,选择了投降。他们目睹了大王庄那场惊心动魄的激战,内心震恐,士气全无,再也不敢应战。
至此,黄维终感山穷水尽,陷入绝境。
蒋介石陷入困境,无奈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胡琏,命他作为12兵团副司令官前往双堆集,期望他能率领残部成功突围。
当初12兵团初创之际,胡琏本应担当司令一职,然而最终却仅得副司令之位。胡琏心中不忿,一怒之下,便以回乡奔丧为名,独自返回故里,隐居起来,看似沉浸在“哀悼”之中,实则不过是在独自发泄心中的不快罢了。
在这危急关头,12兵团濒临崩溃边缘,却未曾料想,胡琏竟在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
此刻,众多人纷纷劝告他:“此处环境极为危险,为何你执意要挑战这一艰难困境?”
即便你投身沙场,仅凭个人之力亦无法逆转战局。最终,你或许只是多了一具战场的亡魂,或是为共军多了一个俘虏。这样的牺牲,难道真的值得吗?
胡琏确实颇具军人本色,他言道:“人生在世,遇到难题自当直面,真若身处绝境,我绝不会被死亡的恐惧所屈服,绝不会因惧怕而退缩!”
经过两日的蛰伏,胡琏毅然决然地闯入了敌方严密的包围圈。
胡琏抵达台湾之际,肩负整理战史资料的使命,便亲自动手,绘制了一幅描绘双堆集战役情景的简易作战图。
此照捕捉了他回忆起自己孤身驾驭战机,翱翔于双堆集上空之时的情景。
土地难免有失去守护之时,而此时,军队的保障作用便显得尤为关键。
这两句的标注清晰地映射出他那时的情绪波动。
说到底,土地的丧失无足轻重,关键在于能够带领队伍走出困境。
在那年的2012年,凤凰卫视的记者专程前往台北,与胡琏的后人胡敏越进行了深入的交谈。此行的目的,正是为了将那场战争的诸多历史细节,梳理得更为详尽和清晰。
胡敏越对记者表示:
那情形确实相当紧迫。黄维在双堆集地区匆忙搭建了一条简易跑道,仅能供小型飞机勉强完成起降。祖父麾下有位名叫石让齐的石先生,他驾驶一架小型飞机,将胡琏安全送达双堆集。
全军将领悉数集结,共同迎接他的归来。众口一词,无不称颂,这位老军长的重返,无疑是喜讯频传,士气也因此大振。
徐克杰与张世礼两位尊长,均为那段双堆集战役的英勇战士。徐克杰曾担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的参谋职务,而张世礼则是在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担任营长的职责。
在那场决定性的双堆集战役中,徐克杰与张世礼携手领军,率领中野和华野的英勇部队并肩作战,最终将黄维、胡琏所指挥的第12兵团击败。
徐克杰回忆过去道:
胡琏在指挥艺术上远胜黄维,其战术灵活多变,颇具匠心。我与您往昔曾多次与其交手,犹记得1946年9月的龙凤之战,那便是我俩首次交锋。
在那场激战中,我们与他们在大王庄这片土地上陷入了激烈的对峙。时而我们奋勇冲锋,时而又迅速撤回,然而不久后,我们又再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
胡琏领兵作战,确实颇具独到之处,战场之上,他更是勇猛精进,敢于拼杀。
胡琏的到访让12兵团的战士们士气大增,然而实际上,该兵团的现状已是岌岌可危,仅凭胡琏一己之力,恐怕难以扭转战局。
尖谷堆,这座屹立于双堆集南边的一座峻峭的小土丘,乃是黄维兵团所剩无几的最后一处防御阵地,与兵团总部所在的马庄仅有咫尺之遥。
大王庄沦陷之后,黄维兵团中的18军残部在尖谷堆一带被围困多日,面对严寒与饥饿的双重折磨,时日愈发艰难。
在黄维兵团的编制之中,第18军第33团有一位名叫廖明哲的少校营长。他与记者展开了一场关于过往岁月的对话。
随着军中粮草的告罄,无奈之下,部队只得动用了战马。厨房内,忙碌的身影匆忙将马肉烹煮至半熟,便火速送往了前线。待到我分食时,仅剩最后两块干瘪的肉块。
我询问那剩余的肉分去向,厨师回答,它们在穿越前方战壕之际,被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们取走了。
死了的人会抢你东西吃吗?
厨师感叹道,众人原本都僵直地倒卧在地,宛如失去生命。然而,一旦诱人的肉香飘至,他们立刻如同脱胎换骨般复活,争相抢夺肉块,大快朵颐几口后,又重新倒回地面。这情景,岂不是宛如死而复生一般吗?
全员此刻饥肠辘辘,根本无力再战。
寒风刺骨,食物匮乏,栖身之所亦无从寻觅。有些人只能就地挖坑,以求在严寒中寻得一丝温暖。另一些人则会搜集高粱秸秆,在坑上搭建起一个简陋的遮盖。若能碰巧拾得降落伞,那自是上上之选,足以搭建出一个更为稳固的庇护所。如此境遇,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。
我真是挺幸运的,经常对家人说,那些所谓的富豪其实远不如我。他们哪里懂得如何用金钱来生火取暖,或是用钱来烧水呢?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,而我却能。
凝视着那处所在,坚守一日的收入可达五万元。南京方面竟以飞机高空抛洒现金。即便生命垂危,这些金钱对我又有何益?我高声呼喊,指示众人打开箱子,取用生火取暖。那一箱满满当当的五万元现金,就这样从天而降。
身处这层包围之中,其景象之凄凉,实难言喻,让人难以想象。即便我竭力描述,也恐怕难以引起大家的共鸣,那种悲怆之情,令人叹惋。
二十余载时光流转,即便是历经沙场的胡琏,每念及昔日情景,心间依旧忍不住阵阵颤栗,恐惧之情油然而生。
胡琏之孙胡敏越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胡琏亲笔所书之物。
战事激烈,双方交火频繁,生死悬于一线,转瞬即逝。距我三百步开外,根本不及援手。
步入暮年,胡琏回顾双堆集之战,将其一一记录。细读其文,不难察觉,彼时的战况紧张至极,双方已陷入肉搏战,战斗之惨烈程度,令人触目惊心。
张世礼,昔日曾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担任营长。他曾与我们分享过那段不凡的往事:
1948年12月15日午后,我军的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发力,对黄维兵团展开了全面的猛烈攻势。
两大主力部队集结了所有火炮,自下午4点半起便展开了猛烈的炮击,炮声震耳欲聋,如同雷霆万钧,将黄维兵团的阵地炸得面目全非。直至5点半,炮火才渐渐平息。随后,在6点钟的号角声中,战士们奋勇冲锋,发起了激烈的攻击。
当夜幕降临至七点钟,黄维的兵团因弹尽粮绝,已彻底陷入崩溃。黄维迅速命令各部队砸毁重型装备,丢弃通讯器材,并将伤员抛弃,随即各自散去,寻求逃生之路。简而言之,全员各自为战,只求保命逃生。
我的营队原本有六百余众,但在突围之战中,仅余下寥寥数人。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拼搏,我们终于突破了解放军的重重防线,安全地冲出了包围。包括我在内,最终幸存下来的,仅有十二名战士。
兵团首脑黄维、副首脑胡琏,以及85军的主帅吴绍周,三人均毅然决然地跃入坦克。在11师及战车部队的严密护卫下,他们于双堆集西侧寻觅到一处空隙,随即猛烈地发起了冲锋。
胡琏驾驶坦克勇猛地冲在最前方,途中遭遇了一座浮桥,他竟顺利驶过。然而,那座浮桥却因坦克的重量而承受不住,最终被压塌。
黄维驾驭坦克,却遭遇桥梁无法逾越的阻碍,只得另辟蹊径。然而,这位军士似乎霉运连连,坦克行进途中竟突然故障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舍车步行,与众多溃散的士兵混杂在一起。最终,在黄沟地区,他被解放军生擒活捉。
胡琏闲逛至鲍集一隅,不期然遭遇了李延年兵团的巡逻队。在他们的引领下,他被带到了蚌埠。如此一来,他意外地避过了一场劫难,成为了那场搜捕中幸免于难的人。
85军的军长吴绍周,驾驶坦克紧随胡琏与黄维之后。不料胡琏的坦克不慎压塌了浮桥,黄维目睹此景,立刻改道而行。吴绍周目睹这一幕,果断地从坦克中跃出,奔至附近的一座小庙,选了个角落稍作休息,心中暗想,待解放军到来将其擒获。
在1989年,黄维曾与美国记者谈及此事,他言道:
12月15日,我们各自踏上逃亡之路,我与副司令胡琏分乘两辆坦克,迅速撤离战场。
行进至约四十余公里的路程时,我的坦克突然失去了动力,停滞不前。面对这一突发状况,我顿时束手无策,只能弃车检查。不曾想,眼前竟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,他们迅速将我控制,于是,我便如此落入了他们的手中。
谈及那次突围的经历,黄维不禁感叹,先是桥梁轰然倒塌,紧接着车辆又突发故障,他勉力疾行四十余里,终究还是未能逃脱,这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。
他未曾料及,自己在深夜时分胡乱奔波,竟在原地兜转了长达40里的路途。从起初逃离的小马庄,到坦克最终抛锚的黄沟,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区区两公里。
步入暮年,黄维方才得知,当年被拘禁之地竟有“黄沟”之名。他顿时喜出望外,连声欢笑,反复提及此名。
果不其然,名与地竞相呼应,黄维竟跌入了黄沟之中!
胡琏在晚年岁月里,大部分时光都在台北县的一座眷村官邸中度过,那里绿意盎然,花园环绕。即便他离我们远去,家人仍保留着他书房的旧貌,一切如故。
胡琏之孙胡敏越,对特地莅临台湾进行采访的记者坦言:
一类论述军事策略,另一类则倾诉其个人传奇。
闲暇之际,他尤为钟爱拆字游戏,常执笔于一张纸,信手写下“双堆集”中的“堆”与“集”二字。
观察“堆”字,你会发现它右侧有个“隹”字部分。同样,“集”字的上部也有“隹”。当他在纸上写下这两个“隹”时,他说,“两个”合起来我们就叫它“双”,而“双”恰好是“双堆集”这个名字中的首个字。因此,“双双”就是这样得名的。
据此解读,黄维本不应落入法网,他与黄维理本应携手重返南京。
他晚年时常常提及,内心深处实则对黄维心生羡慕。黄维得以随心所欲地前往他昔日浴血奋战的土地漫步,随意一瞥,尽收眼底。
然而,他无法前往,一想到现今的双堆集,那片土地定是肥美至极,地底下埋藏着多少生灵啊!
经营杠杆的定义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